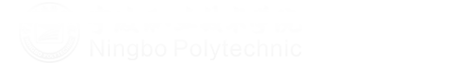“图书馆利用”教育是什么?是读者用好图书馆的一把钥匙。
“图书馆利用”教育的基本内容,主要包括:图书馆环境与馆舍构成、功能区域及对应的服务项目、馆藏所有文献资源的集中式揭示、面向读者开放的基础业务功能利用、图书馆利用信息查询技能培训,以及随知识领域扩充深化与图书馆技术进步、受众以受教育程度递进为代表的自身条件演变与对图书馆利用需求变化所带来的图书馆业务更新,由此衍生的对“图书馆应用”教育内容的更迭和完善等。
“图书馆利用”教育内容是分层次的,主要分为新读者培训、读者基本利用教育、读者个性化利用教育三个层次。
新读者培训,亦称用户培训,通常是面对刚办理读者证,尚未开始独立利用图书馆的读者开展的教育活动,是以集中宣讲方式进行的。
读者基本利用教育,是面向那些有了一定的图书馆利用经验,掌握图书馆利用基本方法,期待对图书馆读者服务功能进行深度了解的读者开展的教育活动,是以集中宣讲和个别指导相结合方式进行的。
读者个性化利用教育,是面向那些能够独立娴熟地利用图书馆,期待利用图书馆专业文献或特色馆藏,或者定题服务、馆际互借等服务方式满足自己个性化阅读需求的读者开展的教育活动,是以点对点服务与服务成果展示相结合方式进行的。
笔者以为,公共图书馆特别是少年儿童图书馆的“图书馆利用”教育,是刚刚走进图书馆准备接受图书馆读者服务的读者,全面准确认知图书馆的必修课,解决的是读者“该如何利用图书馆”的问题;同时“图书馆利用”教育,又是图书馆员与读者面对面进行的,是两者互动的最有效的方式,对鼓励读者留在图书馆、用好图书馆,消除图书馆阅读疑虑甚至障碍有着非常重要的激励作用。
所有的“图书馆利用”教育内容,在图书馆基础业务特别是读者服务工作项目上,都能够也必须与具体环节相匹配,反之“图书馆利用”教育就会成为空谈。“图书馆利用”教育,是伴随读者利用图书馆始终的,是由浅入深、由低到高的。某种意义上说,“图书馆利用”教育,是读者与图书馆之间最有效的互动载体。
笔者最早见过的有关“图书馆利用”的教育文献,是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的、由苏国荣著的《国民小学图书馆利用教育与辅导》和花莲师范学院图书馆印制的、由施冠慨等人合著的《如何利用图书馆》(后者作为图书馆使用手册更合适些)。当然,在诸多专业期刊中,也搜索利用过相关文献,但数量不多。
与时下热度居高不下的“阅读推广”相比,“图书馆利用”教育要小众得多,尤其是当“少儿阅读推广”已经演化成为读者服务工作的重要内容之后,“图书馆利用”教育仿佛成了鸡肋,就连作为行业标准的第六次全国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评估定级中省、市、县三级公共图书馆和少年儿童图书馆等级必备条件和评估标准的具体内容中,原本有过的“读者教育与用户培训”也已无迹可寻。
要知道,少儿读者是图书馆读者群体中的未来,他们如果不会利用图书馆,或者不肯利用图书馆,那公共图书馆将会变成什么模样?图书馆自家人都不肯在让读者“知道用”“会用”“用好”图书馆上花气力,又有什么理由让读者非要用图书馆不可呢?“没有图书馆,民众照样可以幸福地生活;有了图书馆,民众可以生活得更幸福。图书馆并不是民众不可须臾离开的场所,很多人一辈子没有进过图书馆,你能说他们生活得不幸福吗?”(程焕文语)这话说得够决绝的吧。

除“读者教育与用户培训”项目,把“阅读指导与阅读推广”作为“服务效能”的专题项开列,并以阅读指导活动、阅读推广活动、图书馆服务宣传推广为类目进行细分,用学科理论指导本无可厚非,关键是图书馆组织举办这些活动的目的是什么,对到馆读者试图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有着怎样的作用,这是需要认真商榷的。
此间,笔者更信任界内大咖的解读,譬如王波老师对“图书馆阅读推广”的说法,即“图书馆阅读推广,是指图书馆通过精心创意、策划,将读者的注意力从海量馆藏引导到小范围的有吸引力的馆藏,以提高馆藏的流通量和利用率的活动”。“图书馆阅读推广与其他行业的阅读推广的最大区别,是其阅读推广的直接目的是提高馆藏的流通量和利用率,这个直接目的达到后,才能间接发挥培养读者的阅读兴趣、阅读习惯以及提高读者的阅读质量、阅读能力、阅读效果的作用”。
王波老师对“图书馆阅读推广与图书馆利用教育有何区别”的回答也是清晰得很,“利用教育面向全部资源,包括书、人、物。阅读推广只能每次聚焦部分馆藏”。很显然,“图书馆利用”教育是与图书馆阅读推广有区别的。但是,王波老师对“图书馆利用”教育与“图书馆宣传”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却讲得不透,让笔者还是心存疑虑。
譬如,“图书馆阅读推广都属于图书馆宣传,但是如果图书馆的一项活动只是整体上宣传图书馆的历史、建筑、馆藏,不聚焦于某部分馆藏,那么就只能算是图书馆宣传,而不能算是图书馆阅读推广”。“图书馆开展的信息素质教育,因为其目的是引导读者面向全部馆藏检索到自己需要的最精确的文献,指向的是唯一的馆藏或知识单元,而不是小范围的馆藏,指向的不一定是有吸引力的馆藏而是最有用的馆藏,教育的目的是提高检索能力而不是阅读能力,所以也不能称之为阅读推广。”
将王波老师据说中的“图书馆宣传”,与前面提到的评估标准中有关“图书馆宣传”的表述,即重要时间节点的“媒体宣传推广工作活动”及“馆内、馆外利用各种方式开展的书刊宣传推广活动”进行对比,不难发现,两者关于“图书馆宣传”的解读还是有区别的。
另有界内大咖黄俊贵先生于2005年在《完善图书馆读者宣传》一文中言称,“图书馆的社会作用以社会认知为前提,广大读者只有了解图书馆才能更好地利用图书馆”,“向知识受众、社会公众宣传图书馆性质与作用,展示服务内容与方法”,“指导公众对图书馆的认知,吸引社会对图书馆的热爱,动员读者接受图书馆服务,实在是鉴别图书馆管理水平的最为直观的根据,也是评估图书馆作为人文关怀的不可或缺的条件。”笔者以为,黄先生所强调的“图书馆读者宣传”,不只是与“图书馆利用”教育有异曲同工的效应,且更能突出其价值所在。
终归,图书馆是为读者所用的。藏书丰厚,可以为读者阅读节约成本;氛围浓厚,可以为读者阅读培根筑基;示范引领,可以为读者阅读提供样本,这种获得,一定是以读者的“图书馆利用”为发端的。
经验表明,民众对图书馆仅有用的意愿和行为是远远不够的,而且对图书馆的认知和利用是凭借个人亲身体验的自觉进行的,是在“体验(应用)——获得——幸福(好用)”量的积累和经验感悟的循环中完成的。当读者踏入图书馆大门之后,自己可用的服务项目有哪些?能做什么?会得到哪些帮助?图书馆员不讲,或者读者没有认真听,就不会真正的“用好”。这就要求图书馆员在实施“图书馆利用”教育过程中,把馆藏的每一个资源的价值和作用讲清楚,把每一项服务功能讲清楚,使得他们的获得感来得真切,来得踏实。读者在具体应用中获得越多,就愿意应用,就会用得更好,获得感越多,幸福感越强。
需要说明的是,“图书馆利用”教育绝不是你打我通的单向灌输,而是把图书馆展示给读者的一种主动的沟通、交流甚至是思想碰撞的双向互动,彼此互为因果,而且与图书馆诸多基础业务紧密相连,不会脱离图书馆服务效能发挥而独立存在。